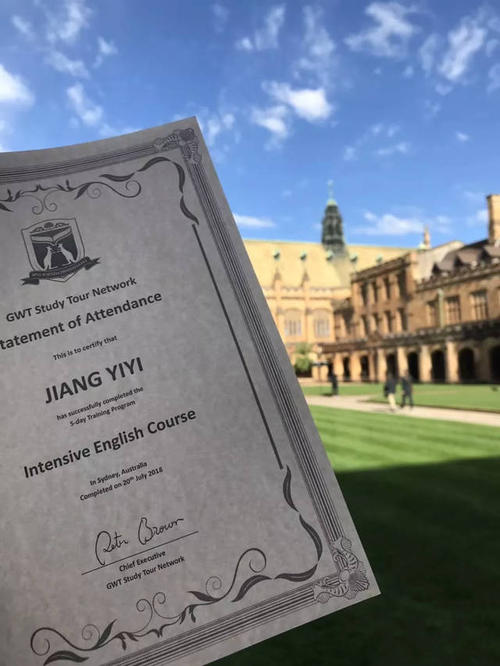俗语道:“戏法人人会变,各有巧妙不同。”读书亦然。回顾诸多名家大师的读书经验,长枪短剑,南拳北腿,各有各的精彩。郭沫若和郁达夫认为,读书要从目的出发,或为学习而读书,或为创作而读书,或为研究而读书等,目的不同,读法不同;而夏丏尊认为,读书应该视不同类别的书而异,不同的书有不同的读法;梁启超、林语堂提倡趣味主义,陈垣、梁实秋则反对读书只凭兴趣,认为要养成苦读的习惯……尽管如此,从名家林林总总的读书经验中,仍可梳理出一些带有普遍性和启发性的“读书经”,以资借鉴。
“随便翻翻”
不少民国名家从小接受的是传统的私塾教育,可奇怪的是,成人后的他们却承认自己真正的阅读启蒙,大多来自小时候那些漫无目的的“杂览”。周作人在《读书的经验》一文中说:“在书房里我念过四书、五经、《唐诗三百首》与《古文析义》,只算是学了识字,后来看书乃是从闲书学来。”后来懂得文章的好坏、思想的是非,是他长期博览古今中外的书籍后“暗中摸索”出来的。
同样,美学大师朱光潜在《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》里回忆儿时的阅读,也是在父亲的教导下,读四书、五经、纲鉴、《唐宋八大家文选》等科举应试的“敲门砖”,但他不满足于此,偷偷浏览了大量“闲书”,从《史记》《战国策》到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厢记》等小说、戏剧,乃至《麻衣相法》等杂七杂八的书,“总之,我幼时头脑所装下的书好比一个灰封尘积的荒货摊,大部分是废铜烂铁,中间也夹杂有几件较名贵的古董。”直到上了大学,朱光潜才开始接触外国作品。然而,正是少时的正规训练和杂览旁收,奠下了朱光潜一生的写作“基因”。
这种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的涉览,即鲁迅颇为推崇的读书法——“随便翻翻”。鲁迅在一次演讲中希望年轻学子们看书首先要“杂”,他将杂览比作游公园,“随随便便去……所以会觉得有趣”。
读闲书,除了轻松有趣,还便于打开视野,增进常识,同时读者能从中摸索出读书的门道,发现自己的“趣味”所在。1923年,梁启超为当时《清华周刊》推荐“国学入门”书目时说:“学问固贵专精,又须博涉以辅之。况学者读书尚少时,不甚自知其性所近者为何。随意涉猎,初时并无目的,不期而引起问题,发生趣味,从此向某方面深造研究,遂成绝业者,往往而有也。”为此,他专门推荐了一部分“有趣”的书,“供学者自由翻阅之娱乐”。兴趣是学问的导师。人一旦找到了契合自己的“趣味”,也就遇见了自己的天赋所在,往往会产生浓厚的探究欲望,乐此不疲,成就一番事业。这也是林语堂所称的“自动读书法”。
今天,人们忙里偷闲之际,喜欢“随手翻翻”手机,上天入地,漫游一番,或刷新闻,或浏览电子书,我以为都算作“杂览”,是一种不错的阅读习惯。
读“基础书”
当然,只凭个人兴味而“随意翻翻”的人,或许能成为“无所不通”的杂家,却很难在某一领域成为行家里手。蔡元培是著名的教育家,也是一位学者。他晚年总结一生的读书经历时,却诚恳地检讨了自己的“不得法”。他说年轻时求知欲很强,“以一物不知为耻,种种都读,并且算学书也读,医学书也读,都没有读通。”到了40岁,一会儿学德语,一会儿学法语,可都不算精通,后来去德国大学学习,哲学史、文学史、文明史、心理学、美学、美术史、民族学,统统去听课,相关的参考书,也乱读起来,终究没能在具体某学科有所建树。蔡元培的话固然是自谦,但其中的道理,足以给读书人一个提醒,那就是读书不可泛滥无边,必须处理好“博与专”的关系,尤贵在“博”的基础上有所“专”。史学大师陈垣在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61届毕业生谈话中,就要求学生做到博与专的“辩证统一”:“世界上的书多得很,不能都求甚解,但是要在某一专业上有所成就,也一定要有‘必求甚解’的书。”
可惜,现实生活中,大部分的读书人都没有觉悟到这点,结果是:阅书无数,一事无成。
读书如何做到“专”?民国大师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,兹列举三点:
一是读“基础书”。随着社会的发展,书籍愈来愈多,单是每年出版的新书就已浩如烟海,某种意义上说,书籍成了读书人的一种负担。朱光潜在《谈读书》中提到,中国古代学者因书籍难得,皓首穷年才能治一经,不过,书读得少,“读一部却就是一部,咀嚼得烂熟,透入身心,一生受用不尽”。而现在书籍易得,一个青年学者就可夸口读书万卷,然而真正“留心”的却少得可怜,还由此养成了浮浅虚骄的习气。至于普通读者,不仅贪多嚼不烂,而且四面出击,拣到篮子里的都是菜,在书海中迷失方向,徒然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因此朱光潜建议,与其读十部无关轻重的书,不如以读十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书,比如浮皮潦草地读许多本谈论希腊哲学的书,不如熟读一本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来得受益良多。著名学者、作家金克木把类似于《理想国》这样的“原典”称为“基础书”,后世千千万万同类书籍就是从这些为数不多的“基础书”里发源的。
二是心中有个远景目标。民国著名学者张其昀说:“为学必先立志,自家有主意头脑,方有以自立。”意即读书人须先立个“目标”,然后才能学有所获,仿佛种树先必有根,再经浇水施肥,最后才可能茂盛生长。否则,读书人“以书为主”,势必被书牵着鼻子走,成为“书奴”,这种阅读往往是迷茫的、低效的。在张其昀看来,读书人心里有个清晰目标地读书,即便杂览群书,也能不迷失自己,并能做到“专而不杂,致一而不懈,故得精通”,好像一个雪球,无论滚多远,都能吸住沿途的雪花,让自己越变越大。
三是“读书必须有一个中心”。如果说“心中有个远景目标”是着眼于长远的、宏观的,这里的“中心”就是比较短期的、微观的。在朱光潜看来,这个读书的“中心”或是某个科目,或是某一问题。如果以科目为中心的,就要精选那一科重要典籍,逐部从头读到尾,以求对于该科获得一个概括的全貌的了解,为进一步的高深研究做准备;如果以问题为中心的,心中先有一个着手研究的问题,然后找相关书籍去读。这种“有一个中心”的读书法,其最大优点在于能做到有计划、有系统性,不至于东鳞西爪,事倍功半。当年,胡适知道顾颉刚生活拮据,有意让他标点古书《古今伪书考》,以便多挣点儿稿费。那是一本小书,胡适以为十天半月就可以完成。哪知大半年已过,顾颉刚还毫无动静。原来顾颉刚对古书中的每条引言,都去翻查原书,仔细校对,注明出处和删节之处等,所做的工作已经远远大于简单的标点。又过了许久,顾颉刚告诉胡适:《古今伪书考》不必付印了,他现在要在标点和研究的基础上,编辑一部疑古的丛书,叫作“辨伪丛刊”。一两年后,顾颉刚再次不满足于自己编辑“辨伪丛刊”的计划,打算自己创作了。后来,果真如胡适判断的那样,顾颉刚成了中国史学界贡献不可限量的大学者。这就是“有一个中心”的读书法所产生的效力。
“读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书”
著名作家、学者曹聚仁在父亲的管教下,从小学开始读《近思录》《朱文公全集》《王阳明全集》,他发现这些书之间存在着不少的矛盾,便询问父亲,父亲也无法解答。到了师范学校,遇到博学多闻的单不庵老师,非常敬仰。再后来,接触了胡适、梁启超、顾颉刚等人的观点,又对单老师产生了怀疑,觉得他虽博学却没有自己的见解,单老师就像沙漠的吸水一样,大量地吸收了知识,却不能喷一点点到地面上来。为此,曹聚仁总结出三条“读书经”:第一,时时怀疑古人和古书;第二,有胆量背叛老师;第三,组织自我的思想体系。
这三条经验中,“怀疑”是基础,也是最重要的。
那么,怎能做到读书有疑?
首先必须不存成见。顾颉刚在《怎样读书》文中写道:读书,是要借助书籍寻出一条求知的路,而非让书来限制我们的思想,读书的时候要随处会疑。换句话说,要随处会用自己的思想去批评它。基于此,顾颉刚提醒读者,读书时不可先存成见,把某一类经典当成标准,而把别的书都通通视为旁门左道。
其次不能偏食,要多读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书。就像喜欢结交与自己“性相近”的朋友一样,很多读者只读跟自己“情投意合”的书,对于那些趣味、观念不相近的书,往往不屑一顾,贬入冷宫。如果单纯为了消遣,这种读法无可厚非,甚至称得上是一种很健康的精神按摩。但从扩大视野、增益智慧看,同质的书读多了,难免出现近亲繁殖的恶果,无异于给自己画地为牢。因此,金克木提出一个主张——多读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书。他说,读“异见”书,“可以使自己瞿然一惊,然后以敌人的态度去观察这本书的意见。结果若是自己被人折服,自然是自己原有的见解不对,从此便更进一步;若自己攻破了书中的理论,也就是自己受到了一次论敌的冲锋,无形中也加强了自己的力量”。这就像习武者,必须经常找高手过招,多挨别人的拳脚,才能获得更快的进步。
陈寅恪是史学大家,也是举世公认的20世纪最博学的人之一。他把“读书贵在质疑”的理念提升到另一层境界。在讲授“晋至唐文化史”这门课时,陈寅恪告诉学生:本课程的学习方法,就是要看原书,获取真实具体的史实,再经过认真细致、实事求是的研究,得出自己的结论,总之,读书一定要养成独立精神、自由思想、批评态度的习惯。
读原书、实事求是、独立思考、自由精神,这是陈寅恪读书、治学的方法,也是他一生为人的根本。把读书、做学问与生命实践融为一体,知行合一,无论环境多么险恶,依然至死无悔,陈寅恪先生堪称读书人的典范。
以上若干“读书经”,是名家读书经验中的一小部分。然而,无论多么独特或美妙的读书法,最终都取决于读书的“人”。1925年,鲁迅应《京报》副刊征求十本“青年必读书”的征文,发表了后来引发争论的一个言论:“我以为要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看中国书,多看外国书。”随后,周作人也发表了《古书可读否的问题》一文。周作人认为古书“绝对的可读”,只要读的人是“通”的。他说:“读思想的书如听讼,要读者去判分事理的曲直;读文艺的书如喝酒,要读者去辨别味道的清浊:这责任都在我不在它。人如没有这样判分事理辨别味道的力量,以致曲直颠倒清浊混淆,那么这毛病在他自己,便是他的智识趣味都有欠缺,还没有‘通’,不是书的不好。”反之,倘若是“未通”的人,即便让他去读什么新书,也会弄糊涂。所以,周作人主张:“我们第一要紧是把自己弄‘通’,随后什么书都可以读,不但不会上它的当,还可以随处得到益处。”读了上百篇民国名家关于读书的文字,周作人这几句话,是我最欣赏的。尤其在当下,每看到有人主张这个不许读,那个不能碰,我就忍不住想起这番话,并深深叹息。
(作者系福建省漳州市东山一中语文教师,出版《先生当年——教育的陈年旧事》《过去的课堂》等)